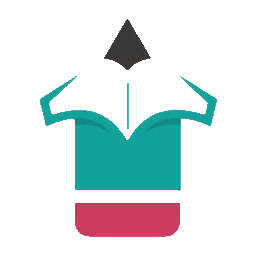因为郑怀看见韩衞随手抓了一块水泥,所以自然是不敢用力的去砍,先是轻轻的一刀劈下。
‘咔’的一声,水泥之上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白印。
嗯?
这水泥显然比我想象的要坚固一些。
想到这裏之后,郑怀又是加大了力度,再次一刀劈下。
‘咔’的一声,水泥之上又再次出现了一道白印。
不应该呀?
难道还是因为我力气用小了?
郑怀这次直接是深吸了一口气,高高的把菜刀举起,狠狠的全力一刀劈下。
耳听的‘咔嚓’一声,水泥之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豁口,而郑怀只觉得手腕被震得一阵发麻,手中菜刀嗖的一声飞到了窝舍裏面。
直接惊动了窝舍里正在休息的几只鸡,受惊的它们顿时是‘咯咯’叫着,冲了出去。
慌得李石赶紧是四处捕捉。
李承乾、李勣见到这个情况,都是一脸的惊诧,这水泥真的如此坚固?
韩衞则是一脸坏笑的看着郑怀说道:
“郑公,手没事吧?”
“是不是菜刀不够锋利,要不要再找个锋利的家伙试试?”
犹自不服输的郑怀听完,连连说好,接着就把眼睛瞄上了李承乾腰间的佩剑。
心裏琢磨:太子配的剑,肯定不是凡品,用来测试这个水泥的坚固程度是再好不过了。
李承乾见到他的目光,也是好奇这水泥到底有多坚固,便解下了腰间的佩剑,递给了郑怀,郑重其事的说道:
“此剑乃名匠之作,名为‘龙泉’,剑锋三尺七寸,净重七斤四两,削铁如泥。”
“暂且交给你来试上一试。”
郑怀听完这话,心中大喜,如此宝剑,必然能把这水泥给劈豆腐一样劈成两半。
想到这裏,也是郑重的接过长剑,口中说道:
“谢殿下赐剑。”
说完揉了揉还有些发麻的手腕,攥紧长剑,气沉丹田,大吼一声,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恶狠狠的一剑朝水泥劈去。
几人只听见‘啪’的一声,那龙泉剑已经是劈进了水泥之中。
嗯,真的很不错。
竟然足足劈进了一寸有余。
郑怀这会顾不得被震得发麻的胳膊,揉了揉眼睛,晃了晃脑袋,确认自己没有看错。
这才惊呼一声,扭头死死的盯着韩衞问道:
“国师,这水泥制作耗费钱财多吗?”
韩衞摇了摇头道:
“不要钱,石灰岩是后山采的;铁矿石是太子送的;黏土是在大堤上挖的。其他……”
郑怀听完有些激动的说道:
“竟然这么便宜。”
“国师,不知道这个搬运成本高吗?”
韩衞再次摇头道:
“不高,主要就是搅拌的时候需要个力气大的,其他的就是一些简单的搬运,谁都能干。”
话音还没有落地,郑怀已经是冲到水泥面前,也顾不得上面的鸡屎,死死的一把抱住,状若疯癫的喊道:
“天啊,这是国之重器呀。”
“造价如此便宜,用人成本又低,它完全可以被广泛采用。”
“盖房、修路、筑墙、建大堤……,可以用的地方简直是五花八门,多不胜说。”
就在说话的功夫,李石把那几只鸡给抓住了,重新给扔进了窝舍裏面。
这不禁让郑怀有些不解的看向韩衞,问道:
“国师,这是什么意思?你竟然用这么好的东西建鸡窝?”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简直是暴餐天物,我现在就要上本参你。”
韩衞摸了摸头,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道:
“倒也不是有意为之,主要是改完澡堂之后,还剩下一点,就顺手给改成鸡舍了。”
李承乾见此,也是赶紧打圆场道:
“算了,算了。国师是个修道的,他虽然发明了这个水泥,但是用途他也不清楚。”
“再说这东西还是在实验阶段。”
“既然坚固有保障,我等会让国师教一下怎么做的,咱们到时候去汴梁批量生产,堵住大堤就行了。”
郑怀这才作罢。
而韩衞听完李承乾要堵大堤的时候,则是皱起了眉头道:
“就是堵吗?”
李承乾摇了摇头,开口道:
“事情挺多的。”
“堵大堤,赈济灾民、查找洛天一掘堤的原因……”
一旁的崔宁也是在旁,自信的补充道:
“还是以堵为主、以疏为辅,把金水河的洪水引到汴河、五丈河和惠民河这三条河道裏面。”
“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洪灾的问题。”
“也才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。”
他说完这话之后,李承干和李勣也是连连点头赞许。
李承乾更是满意的看了他一眼,心中道:
这崔宁虽然出身五姓七望,但却完全没有大家族子弟的架子。
更难得的是,做事愿意亲力亲为,从守护醴泉就能看的出来。
这样的人才,必须要加以重用。
韩衞听完之后,回忆起《河防述言》讲的内容,再次皱眉问道:
“那沉积在河底的泥沙如何解决?”
这句话顿时把崔宁给问懵了,他稍微迟疑了一下,便再次自信的开口说道:
“泥沙,泥沙自然是随着河水冲走了。”
“国师没有治过水,显然是不清楚裏面的东西。”
说完之后,又在心裏狠狠的鄙视了一把韩衞:
你一个偷挖大堤的外行跟我一个内行讨论治水,这简直是自取其辱。
却没有想到韩衞看着他,真诚的说道:
“崔主簿,你可能治河的时间短,有些情况还不太清楚。”
“治水先治沙。泥沙是黄河水患的一个重要源头,随着上流泥沙被水裹挟而下,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聚集堆积。”
“长而久之,泥沙堆积的越多,水势也就越高,堤坝就难以承受压力。最后导致堤坝崩溃,洪水奔涌而出,淹没农田房屋。”
“所以堵和疏都是解决一时的问题,要想黄河长治久安,还是得以堵为主、以疏为辅、以堵促疏的办法。”
崔宁听完之后,犹自不信的说道:
“国师有些危言耸听了吧?”
“自从大禹治水以来,历朝历代治水都是以堵为主、以疏为辅。”
“这黄沙淤积一事还不曾听说。”
同时心中又再次狠狠鄙视了一把韩衞,这肯定是那天在大堤下面被我训斥过之后,找其他人问过治河的事了。
只是这术业有专攻,在治河一道上,你和我之间的差距可是无限大。
韩衞则是认真的想了想,开口道:
“黄河从上游携带大量泥沙进入中下游,确实有一部分是被黄河带走了。”
“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淤积在中下游的河道里,随着泥沙越来越高,水位也会越来越高,特别是到了汛期,河水猛涨,就会有决堤的危险。”
“所以就不得不断加高加固堤坝,这也导致河床与两岸地面的高差越来越大,潜在的洪水威胁也不断增加,一旦决口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崔宁听完之后,觉得韩衞说的似乎有理,但是反覆思索了一下,发现自己看的治水方面的书籍没有一种是韩衞提出的这种观点。
便不服气的开口道:
“敢问国师,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说的这一切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