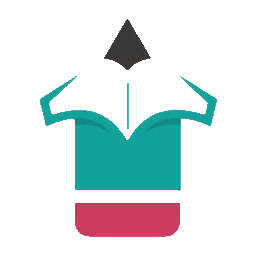第355章 三方博弈,变故丛生
议事殿。
陈洛踏入其中,不由一阵恍惚。
他上次站到这儿,要追溯到什么时候来着?
似乎是文帝朝初年,自己担任代国国相,于年尾携礼前来贺岁。
距今已过四纪。
而这间议事殿内的装潢,相较曾经,亦是发生了较大的改变。
如果总结它的发展变化的脉络。
那么高祖朝为初级阶段。
这一阶段只搭建了宫殿的基本框架。
毕竟大汉最开始的那些年里,要恢复生产,要鼓励商贸,还要和匈奴、南越打仗。
国库里面每一串铜钱都是萧何用日益稀疏的头发换来的,用来大兴土木,修筑装饰宫殿,实在让人于心不忍。
第二个阶段则是惠帝朝和文帝朝,在这两个时期,宫殿内偶尔会添加些必须用品,没有发生过质的改变,故而它们可以归纳为同一个阶段。
刘盈在位的前几年,一年在长安城内甚至待不满八个月。
何况他对于豪奢的装饰没有兴趣。
因此议事殿便一直延续了高祖时期的粗犷风格。
至于刘恒,就更不用说了。
连只需要花费百金的露台都舍不得修,将议事殿翻新所需花费的财物,十倍不止,他又怎么可能花那些小钱钱呢。
因此直到景帝继位的时候,这间议事殿仍保存着最原始的“风貌”。
不过进入了第三个阶段,即景帝朝时期,这间议事殿终于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大殿的主体属于木质结构,经过几十年的雨打风吹,有些地方多少会开始腐朽,即使不至于出现安全问题,但看上去多少会有些碍眼。
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积累,刘启在位的中后期,国库里的铜钱几乎快要堆满。
修缮宫殿需要的钱粮,可谓九牛一毛,不用背负太大的心理压力。
不过刘启延续了阿父节俭的意识。
哪怕他手里有了足够的钱粮,也没有新建行宫与猎场,仅仅打算将宫城内部主要的十余间宫殿给翻新了。
不过有臣子提出建议,说长安乃是大汉的国都,宫城更是长安的心脏,作为大汉的象征,四方诸侯朝拜天子之处,需要有威仪。
刘启觉得颇有道理,于是令工匠在翻新的时候,顺便增加了部分装饰。
距离上次翻新,尚未过去十年。
因此陈洛再次踏入殿内,会有焕然一新之感。
用眼角余光打量了小会,他便随群臣行礼坐下。
自己这次过来,不是观光旅游,而是有正事要做。
将胶西王定罪,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对方作为诸侯王,之前敢派人拦路截杀使团,没道理在这最关键的时候,选择摆烂等死。
随着几件琐碎的小事讨论结束,刘彻扫视群臣道:“诸位应该听闻了胶西国夷安县一案吧?大汉七十余载,从未有过。
而朕继位不到两年,就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情,难道是因为朕的德行不够,触怒了上天吗,惹起了民怨吗?”
这话一出,底下群臣皆深吸了口气。
看来这件事情,陛下不打算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啊。
不然完全没有必要将话说得这么严重,简直没有留下太多退路。
此时,王臧站起,语气愤慨道:“陛下,臣以为这件事情不能怪罪到您的身上,您登基以来,无时无刻皆在为大汉思虑,为黎民谋福祉,谁敢说自己的德行能够超过您呢?
而常言道主辱臣死,您若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哀伤,那臣愿意为此付出生命,来提您分担忧愁。
胶西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,臣认为应该问罪到具体之人,严肃处理。”
好家伙。
群臣更加确定了他们之前模糊的猜测没有错。
要知道王臧作为皇帝的心腹,在正式商议这件事情之前,肯定在私下就有过探讨。
在一定程度上,他的发言就可以代表刘彻的意志。
“王郎中如此,朕甚是欣慰啊。”果不其然,上首位置传来认可。
顿了顿,刘彻接着道:“朕之前派专人前去调查,当下已经返回长安,赵大夫,你来说说结果吧。”
闻言,赵绾就站起道:“陛下,臣弹劾胶西王,前段时间您派出去调查的队伍,将结果整理汇报上来,胶西王这些年在封国内,的确称得上是胡作非为。
这次夷安县内的百姓之所以冲击县衙,即是因为胶西王提前征收刍藁,导致百姓心生不满,而后续胶西王命令地方强行弹压,没有处理得当。
最后便出现了这起骇人听闻,前所未有的案件。
臣建议严惩胶西王,以平民怨。”
随着赵绾话音落下,他的身侧又有人起身。
“禀陛下,臣不同意赵大夫的观点。是那些百姓暴动,杀死了当地县令,岂能怪罪到胶西王身上呢?固然有刍藁的原因,但谁能说不是那些百姓心存反意,恰好找出的理由?难道赵大夫是与那群暴民共情吗?”站起这人乃是丞相卫绾,不过他并非由刘彻直接任命,而是从先帝时期就开始担任这一职位。
故而他代表的利益,和刘彻并非完全一致。
现在他站起来为刘端说话,让朝中群臣的目光带上几分玩味起来。
看来这事好像还有得扯皮啊。
尤其是最后那句话,乃有诛心之意。
赵绾自然不满头上被扣了顶帽子,当即反驳道:“在圣君治下,百姓安居乐业,受到教化,岂会心生反意,可面对不公正的暴政,百姓的反抗难道不是应该的嘛?
太祖高皇帝正是不满暴秦,故而推翻了他们的统治,建立了大汉。
卫丞相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吗?”
面对赵绾咄咄逼人的态势,卫绾忠厚老实的面孔中浮现出一抹轻笑。
他眯眼道:“哦?难道按赵大夫的意思,当今并非圣君治天下嘛?”
对于核心观点避而不谈,但他抓住了语言上的漏洞。
顿时,赵绾脸色涨红,还是王臧站起解围道:“胶西国由胶西王治理,发生这样的事情,故而赵大夫才会弹劾胶西王。”
虽然用这个理由解释过去,但刘彻的脸色并不好看。
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,自己这两个亲信在正面语言交锋上,实在逊色太多。
因此赵绾和王臧丢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面子,而是他这个天子的面子。
“陛下,我携胶西国相文书,历经险阻,终于送至长安,请您将它公之于众。”在这尴尬的氛围中,陈洛忽地站起。
即使朝堂内的群臣无人认识他,但实际上起到了岔开话题的效果,算是替刘彻解围。
而且照目前的局面来看,想用夷安县的事情将刘端摁死,完全没有了可能。
那么胶西国相的文书就可以成为另外的火药桶,再度引爆整个局面。
仅怔了一瞬,刘端马上反应过来。
顿了顿,他肃然说道:“说的不错,胶西国相的使团历经艰险,方才抵达长安,将这么一封满含血泪的文书,送到了朕的手中。朕希望诸位一并来听听。”
接过陈洛的话头,默契地将话题完美岔开,不再去讨论卫丞相刚才言说的内容,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对方继续利用优势穷追猛打。
而刘彻在拿过案牍上的那封文书,正式将其展开前,瞥了底下起身直言的那名年轻人一眼。
似乎是叫陈珣来着?
果真是一块璞玉啊,表现甚是机敏。
留下这般初步印象,刘彻照着那封文书,缓声念了起来。
“……宫中常死宦者,血肉模糊……国中常传,前国相饮鸠而亡……知王上所行,臣甚恐慌,日夜惶恐,常掩面而泣,望陛下明鉴此事。”
“这封文书,是胶西国相三个月前送来的,至于为何前两日才由赵大夫转交到朕的手里,是因为使团在途中遭遇了数次匪盗截杀,嗯,诸位怎么看?”
刘彻目光冷冷地扫视全场。
殿内一片死寂。
群臣无言。
这是要出大事的节奏啊。
胶西王行事颇为荒唐,他们亦有所耳闻。
之前刘端被弹劾的时候,先帝并未降下责罚,外加齐地离关中甚远,让很多大臣对于这位诸侯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。
但胶西国相的文书上的记载被念出来,让众人又有了新的体会。
不寒而栗。
人性之恶,为何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?
他怎么敢这样对待朝中的臣子、治下的百姓啊?
有资格上殿的大臣,基本已经坐到了中高层的位置。
只要不是过于年老或者说皇帝心腹,谁都不敢说自己未来没有外派到诸侯国中担任国相的可能。
若碰见像刘端这样的诸侯王,恐怕真就会“日夜惶恐,常掩面而泣”。
这时候,原本替刘端辩解的卫绾脸色亦是发僵。
坑货啊!
这怎么做到让国相都上书举报的啊?
要知道刘端托人送来一封书信,让自己看在先帝时结下的善缘,出面求情。
外加有人暗示,卫绾最终愿意出面,顶着刘彻的压力争辩。
结果没想到反倒被刘端狠狠地坑了一道。
这封文书出来,他前面的辩解完全被打了个粉碎,无论接下来自己用什么说辞去求情,都会显得那般苍白。
而且他已经感受到周围不少望向自己的目光颇为不善。
继续替刘端说话,恐怕会引起众怒。
罢了罢了,自己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,刘端这事,不是自己可以干预得了的层面了。
想到这,卫绾不由得回首望了望刚才起身发言的那名胶西使者一眼。
此子不简单啊。
进场打断节奏的时机刚刚好,自己原本想说的话,全部被堵在了嘴里。
哽得难受。
“诸位,胶西王疑似杀害大汉官员,而暴政引得百姓暴起,可谓天怒人怨,虽然他是朕的兄长,但朕亦不能宽恕他的行为,这件事情应该按照大汉律法定罪,诸位以为呢?”刘彻见众人尚处于震惊之中,无暇应答,于是直接开口,给此事定论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没有臣子敢提出反对。
万一自己求情,那赵绾或王臧起身来一句“汝去胶西为相国可好”,该如何回答?
按照文书上的说法,去胶西国担任国相,真是和送命无异啊。
不过就在群臣打算商议如何给刘端定罪之时,殿后出来了一名宦者,手中捧着淡黄色缝制赤色边线的帛书,突兀地打断了朝会的进程。
刘彻眯了眯眼,认出对方是太后宫中的侍者,询问道:“大母可有事否?”
宦者先行了一礼,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宣读道:“禀陛下,太后有旨如下。
端儿有罪过,但他乃您的兄弟,一尺长的布,都可以缝合在一起,那么你们兄弟二人,何必闹别扭呢?
依老身的意见,哪怕端儿有罪过,但希望不要做得太过难看。”
朝堂内的众人简直麻了。
他们完全没想到居然还有反转。
原本按刘彻的意思,他们给刘端大汉律法定罪,不留情面,这件事情就算做了了结。
结果太后一封旨意送出,又明摆着要保胶西王刘端。
要知道大汉以孝治天下,太后甚至有资格使用“朕”这个皇帝的专属称呼,哪怕刘彻贵为天子,亦需要尊重窦太后的旨意。
队列中的陈洛眯了眯眼,意识到事情将再起波澜。
如果一切将朝着预料之外发展,那么自己则需要启用新的手段,去保证结果仍旧符合最初的料想。
在陈洛思索的同时,从属于太后一派的朝臣,已经开始起身发言。
“禀陛下,太后所言极是,您和胶西王毕竟是血肉至亲,这次犯下了错误,可以谅解一次嘛。”说话这人名为窦婴,乃是窦太后的侄子,所以他这番话带了些外戚的立场。
至于其他不沾血缘关系的朝臣,发言则稍稍保持了分寸感。
但他们表达的核心意思没有改变。
那就是不值得因为这些事情,就严加惩戒胶西王,应该从宽处理。
那么刘彻应该收回开始的决定,给刘端一个改过的机会。
舆论的天平再次倾倒。
所以刘端的事情该怎么办?
彻底没了主意的众人,望向上首位置的刘彻,等待这位少年天子的答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