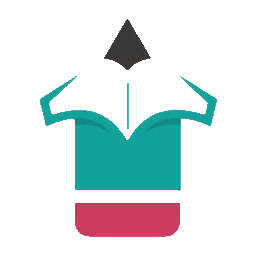第359章 刘端,胶西厉王
群臣在早朝时齐齐弹劾胶西王,无疑形成了一股“势”。
刘彻很聪明,他明白自己可以借着这股力量,彻底将胶西王给按死。
于是接下来定罪的流程走得很顺利,根本不需要反复拉扯。
一来是刘端犯的事情实在够多够重,按照律法定罪,直接可以按最高档的规格来。
原本高祖时期留下了规矩,诸侯以及彻侯除谋逆大罪外,可以免除死罪。
但刘端鸩杀了数位朝廷两千石的大员,真按死理来论,完全可以认为他有谋反的企图。
二来没人想再为刘端申辩,定罪流程走得无比顺畅。
要知道从高祖朝开始,朝堂上就一直存在派系,又因景帝采用权术制衡之手段,让纷争更加明显。
很多时候某一名朝臣反对某项提议的原因,并非不同意这个观点,而是敌对派系的人上书支持它的执行。
正是有这种纯粹为反对而反对的存在,让这议事殿内很久没有出现过整齐划一的论调。
刘端这次达成的成就,可谓前所未有。
三日后。
刘彻将诏书正式下达,除国胶西,黜刘端为庶民。
当使者带着这道旨意离开长安时,甚至配备着军队护送,让众人明白此事彻底成了定论。
但这胶西王一案,绝不能当做孤立的事件来看待。
敏锐的朝臣,在私下里进行全盘梳理。
通过时间线来进行盘点,这件事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先帝时期,刘端受封胶西为伊始。
单论刘端彻底爆雷的开端,则是胶西国相派出使团,上书弹劾刘端。
而整个过程中,又有三个关键的节点。
其一是夷安县百姓暴动。
这让天子打算调查刘端,并发现诸多疑点,加上胶西使团呈上文书,于是决定降罪。
其二则是太后传旨阻饶。
窦太后参与其中,代表着此事不再只是中央和地方上的矛盾,更有中央高层权力的内部斗争掺和进来,也让原本平稳的发展,出现了波澜,刘端差点逃过一劫。
其三即那个叫陈珣的使者坦白身份,给了胶西王致命一击。
大汉宗室派人行刺阳夏文贞侯后人,这事若被有心人传播,那可是要动摇国本。
人心的力量从来不容忽视。
阳夏文贞侯受到先帝推崇,受到大汉无数百姓和官员敬仰,再加上阳夏陈氏近些年里,并未犯下过任何错误,名望可以称得上深入人心,在东南地区尤盛。
当年陈胜在大泽乡举事,即是举着项燕的名义。
要是不处理刘端,焉知未来会不会有人举着为陈氏鸣不平的旗帜,起兵作乱。
明智的统治者绝不会给国家留下这么大的隐患。
故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,刘端不再有任何机会。
哪怕窦太后,都选择袖手旁观,没有继续替他求情。
不过朝臣们并未忽视胶西王一案的后续影响。
毕竟胶西国除,只要刘端没有疯狂到起兵造反,中央和地方上的矛盾算是彻底解决。
可高层权力的内部斗争,尚未结束。
原本大部分朝臣的觉得只要窦太后活着一天,她靠着辈分与“以孝治国”的基本国策,天子想要真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绝无可能。
但经过此案,他们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陈珣即是变数。
他公开支持皇帝的决定,支持将胶西王定罪,就足以说明他并不属于太后的派系。
何况此人的身份绝不容忽视。
当下阳夏陈氏并未有其他嫡系子弟在长安出仕,那么陈珣的态度,是否可以代表着阳夏陈氏的某种态度?
倘若他真能够代表整个阳夏陈氏,那么原本在太后和皇帝中间摇摆的官吏,全部会迅速倒向刘彻。
这就是阳夏文贞侯留下来的影响力。
……
胶西王除国的消息,乃是由信使加急送往齐地,并且配备相当数量的军队护送,路上没有片刻耽搁。
加急送信,乃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先将消息传到胶西,不让刘端拥有太多的反应时间。
兔子急了还会咬人,狗急了还会跳墙。
诸侯王若得知自己被黜为庶民,万一内心接受不了,选择起兵造反咋办?
因此将诏书尽快传达到胶西国去,解除刘端的权力,可以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。
至于为何配备军队护送,那道理就更加简单。
毕竟刘彻担心路上出现“匪乱”嘛。
到时候有人截杀信使,破坏了这道旨意下达,指不定又会惹起新的波澜,导致这件本该平稳落地之事,再生变故。
不过使团赶路过程畅通无阻。
各地郡守县令知道他们的身份后,不敢为难,一路大开绿灯。
自己若是做出什么令人误会的举动,天使回去提上几嘴,让陛下以为他们是刘端同党咋办。
那可不得了。
当使团如风般驰入高密城,宣布刘彻降下的旨意时,胶西朝堂上的所有人都懵了。
啊?
这是什么情况?
尤其是称病久未上朝,得知长安终于又传来诏书的胶西国相。
他听着文书开头,知道刘彻降罪下来,颇为惊喜。
自己派使团送去长安的文书真起到效果了?
不过得知下文的具体内容,他觉得脑袋里顿时成了一片浆糊。
我的要求只是将自己调走,不再于胶西国担任国相,怎么陛下直接把胶西国都除国了?
虽说自己的目的好像同样达成。
毕竟胶西国都无了,自己可不是担任不了胶西国相了嘛。
但是自己这愿望实现的过程,未免有些太过夸张。
而且自己担任个国相,把国君给整除国了,还有哪位上司愿意收下我这个下属吗?
心绪复杂的胶西国相,一时间不知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。
与此同时,刘彻觉得晴天霹雳。
他从使者手中接下那封诏书之后,整个人浑浑噩噩,再度清明,已经回到了后宫之中。
望着熟悉的装潢,刘端明白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居所。
为何如此啊?
明明我早就派人前去劫杀那该死的使团了,明明我专门写信向太后哭诉了,明明卫丞相也答应帮助我了,那些暴民闹事根本不该影响到我,怎么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?
他恼怒地想要打砸周围的一切,却又无力地垂下脑袋。
起兵造反的念头在刘端脑海中闪过。
可刘端悲哀地发现,自己真要选择造反,似乎没有谁会选择跟随。
宫中的宦者和侍卫,畏惧于之前胶西王这个位置的权势,方才听从自己指令。
而他现在丢掉了王位,那些人恐怕根本不会再搭理自己。
朝中的那些大臣与将军,大多内心都带有怨恨吧。
虽说敢于直言者都基本被自己杀了个干净,但每次朝会时,大部分人脸上的淡漠,刘端仍旧看得清清楚楚。
想靠着这些人起兵造反,恐怕他们第一时间就会倒戈,拿自己的脑袋去长安换取功劳。
至于那些想搅乱天下的阴谋家,自己并不认识。
何况就算认识,对方会选择投资自己的概率,应该接近于无。
昏昏沉沉的刘端,走到寝宫内。
他趴在那张锦绣大床上,觉得四肢无比寒冷,黑暗的墙角渗出冷意,朝着自己侵袭而来。
刘端睡了过去,他再度睁眼,内心的焦虑没有得到丝毫缓解,抬起头来,只感觉墙上、梁柱上、天花板上布满了鲜血。
而墙边站满了阴暗的影子。
那些曾经被自己杀死的妃子、宦者还有侍卫,聚在那边,用泛白的眼睛冷冷盯着他。
“你们?怎么是你们?”刘端瞪大了眼睛。
那些影子没有回答他的问题,仍旧用冰冷的目光凝视着他。
刘端宛若疯魔地凄厉吼叫着,呼唤侍卫,却没有人做出回应。
宫内的宦者和侍卫得知胶西王被废为百姓后,早就喜笑颜开地离去了。
没有人再关心刘端接下来的情况。
心生恐惧的刘端翻箱倒柜,想要找来一把利剑,驱散这些阴影。
但他倒腾半天,只在屉中找出半包灰红色粉末。
“呵呵,哈哈。”刘端胡乱笑着,颤颤巍巍地把它们倒入酒中,一口饮下。
渐渐的,刘端觉得自己眼前的世界不再是血红色,只是肚子有些绞痛。
“砰咚。”
随着一声闷响,这位残害无数人的胶西王,怀揣着恐惧,感受着剧痛,倒在了自己的床边。
直到五日后,才有人发现这具腐烂发臭的尸体,随意捡拾着,丢到城外给简陋地埋了,但因为埋得不深,在一场暴雨过后,骨骸不知被冲刷到哪里去了。
……
待到胶西王饮鸩自杀的消息传到长安时,没有引发任何关注。
在政治上,刘端在被除国之时,早已经是一个死人。
他这次饮鸩自杀,更是坐实了之前的全部罪名,其他人连替他翻案的心思都不会升起。
至于主导了整个胶西王一案中三个关键节点的陈洛,正在郭解府上,悠然品茶。
“……刘端这次一死,反倒不用让我们再出手了。好了,伯玉兄,我在离开前再次声明,阳夏陈氏承认了你的身份,并且支持了伱之前的所有行为,而且按照正曲公和若愚公的意思,只要你不行恶事,不害百姓,那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举措。”坐在他对面那人,名为陈旭,取字东升,乃是阳夏陈氏四代子弟。
他前来长安,目的就是考核确认了陈洛的身份。
最后陈旭通过那半枚玉佩,彻底确认了陈洛乃是阳夏文贞侯兄长的后代。
而这次陈洛在胶西王一案中的表现,更是为他赢得了代表阳夏陈氏的权力。
陈洛微笑着点了点头,语气略带欣慰道:“好,我在长安这边将琐事处理完毕,就会尽快前去阳夏,前去祭拜阳夏文贞侯,以及面见家主。”
“嗯嗯,那我就先走一步,回阳夏去给大父他们汇报这件喜事了。”陈旭应答,起身告辞。
不过他老是有一种错觉,即是面前的伯玉兄望向自己的眼神中,莫名有一股……慈爱?
就像是当年大父见到自己作的文章不错,投来的那般目光。
应该是错觉吧?
待到陈旭离开,李序同样进入屋内。
“你不会也是来次辞行的吧?”陈洛抿嘴问道。
李序笑着摇头:“伯玉兄猜得恰恰相反,原本胶西王这件事情忙完,我应该去往齐地或楚地,但是他们觉得我在你身边可以提供部分帮助,负责联络等事宜,于是让我留了下来。
所以伯玉兄,以后就得多多指教了。”
说罢,他拱手行礼。
“指教谈不上,但李兄在我身边,我很多事情也可以放心去做了。”陈洛拱手还礼,又开了句玩笑,“倒是李兄别把我吃穷了就行。”
李序应该是墨家和阳夏陈氏商议好,安排在自己身边的。
陈洛对于这个安排,并不反感。
毕竟自己的存在对于阳夏陈氏和墨家来说,较为陌生,想要赢得完全信任,需要更长的时间。
因此他们安排李序这个内部成员留在自己身边,可以确保自己不会胡作非为,污来了阳夏陈氏的名声。
至于陈洛,身边有李序的存在,亦是多了不少便利。
他现在身边可用的亲信不多,总不能面对全部的事情,都去亲力亲为。
一方面是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,另一方面则是分身乏术。
有了李序在自己身边,部分较为重要事情可以交给他去做。
而后,郭解又推门而入。
他冲着陈洛道:“伯玉,宫中来人,说是陛下唤你前去,这次应该就是想对你进行正式考察,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啊。”
经过胶西王一案,又有阳夏陈氏身份加持的陈洛,现在已经成为了长安城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。
陈洛眯了眯眼,看不出任何紧张地站起身来,点头应声:“明白了,我这就去。”
————
胶西王性残暴,为百姓恨,为天子耻,立国二十三年,群臣弹劾。
故国除,地入于汉,为胶西郡。
端畏,自鸩。
胶西百姓皆未悲。
上闻之,谥为厉王以罪。——《史记·五宗世家》